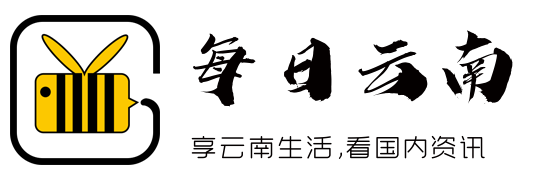闲书拾遗——疫情清理 舞蹈行业先繁荣
一
新冠肺炎肺炎席卷全球,香港当然不能幸免。显然,疫情传播衍生出来的东西,无论从哪里来,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所以世人如此担心,不言而喻;当然,作者也陷入了这种困境,但他甚至从中获得了一点“乐趣”!
香港所谓的“舞(歌)团”是受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前加上“所谓”二字,是指其舞蹈与正道和健康无关,即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卫生署于2000年合办的“社区体能测试计划”中,鼓励香港人进行“跳舞”,这是“全民健身”运动之一(其他可以改善体能和健康的活动是跑步和远足)。也就是说,本文提到的舞蹈是一种休闲班在舞蹈中做运动的交谊舞!作者之所以“好玩”,是因为“舞团”出了大新闻,勾起了作者对舞蹈的绝缘,找出了他小时候闲看的与舞蹈有关的专著。看了之后很有意思,相信疫情过后经济复苏最快的行业是体育舞蹈(“竞技”舞蹈由交际舞发展而来),是面向大众和私人的,所以我做了这篇文章。
真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那本没别人写的灰头土脸的书《合拍——人类史上跳舞和演练的历史》(《在时间里保持在一起》:《人类历史上的舞蹈与操练》)。是芝加哥大学的加拿大裔美国历史学教授W. H .麦克尼尔(1917-2016)写的《瘟疫下的日常》(瘟疫与民族),他的名著《西方的崛起》(西方的崛起)是很多文人都涉猎过的巨型结构。作为一个经常和实体书(不等于“刨书”)作伴的人,这种“奇遇”带来的“惊喜”,是因为疫情而不由自主地重新学习的意外收获。

《合拍——人类史上跳舞和演练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
二
盘古之初,人类可以不说话,可以跳舞。当然只是牙牙学语,指指点点,就是身体随着声音摆动,但是人类学家——可能会说人种学家更合适。——把前者定义为音乐,把后者定义为舞蹈!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歌舞与时俱进,成为原始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歌舞具有“形成人类社会群体团结的象征”的功能,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丧葬仪式、士兵演习、解闷、解闷、健身(美),甚至以此为起点,这种“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其他特征的动物(动物)。——动物也会成群猎食(求偶和交配)踢腿(又大又笨的大象会跳舞),但只会嚎叫和嘶嘶声,不会唱歌,更不会放音乐,这些都是优于人类的“特殊功能”。
显然,在社会生活时期,人类会在狩猎前后围着篝火或对着太阳“唱歌跳舞”。所以人物塑造是祝大有成就,满载而归的庆祝,深层原因是为了表现部落权贵团结一心(穆斯林邦联),让百姓不吃肉不吃肉,在冒险进入森林杀兽前展示肌肉和勇气.这种原始的动机,随着文明的进步,当然成为了一种保健炫耀和社交活动。
舞蹈与人类共存。以作者有限的阅读,最早记录舞者象形文字的似乎是罗马帝国。很多年前,它还在上升。为了理解“手语”的形成,我读了《古罗马的手势和欢呼》(g . s . aldrite :《古罗马的手势和交流攀登》),并举例说明和解释了罗马人的肢体语言。虽然大多数表达方式是“政治观点”,但“手势”类似于今天聋人使用的“手语”。这种“手势”,伴随着音乐,演变成舞蹈,很自然。看完这本专著,突然想起在西方“握手为礼”的习俗传入中国之前(据说是清末孙中山传入的),中国人见面时,男人都是以拱手、鞠躬、鞠躬为礼;在儒家男女授受、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下,女性遇到了男性,直到宋代,她们表演李万甫,女性修剪衣角,“双手交叉于胸腹之间,微屈双膝,微屈右腿背,微鞠躬,说万服”。到了明代,万福礼演变成“右手轻搭在左手背上,将此式移至右腰,左腿前移半步,身体微弯,头低,口称伏完”。因为中国戏曲的流行,李万甫随着音乐而动,手指、手腕、手肘、手臂、肩膀、眼睛、腰、臀部甚至腿都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回缩,产生节奏感和节奏感,表现出女性的“优美姿态”,李万甫演变成了舞蹈!
>三《合拍》第四章论宗教仪式与跳舞源起,有一插图,为见于法国三兄弟穴洞(Trois Freres,1990年前后发现此洞穴的探险家有三男孩,因名)的人脸鹿头怪兽合蹄摇角双腿踏步的壁画(十多年前笔者夫妇与一众友人于南法乡间觅食时曾路过此洞穴,惟“志”不在此,匆匆出入,不见此图;执笔时登入维基百科,见此条并附多幅如见于《山海经》的灵兽乱舞图),成于一万一千多年前,以此推论,当年原始族群已有刍型的舞蹈;作者还示多帧元前若干千年在其他地区发现先人手舞足蹈图像的古物,在在显示舞蹈古已有之……颇出笔者意外的是,《合拍》第五章谈政治与战争,指出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在浙江义乌操练士兵时“旌旗之色、金鼓之音”,以至以战(马)车布防的阵势(令人不期然想起好莱坞电影中以蓬车为阵和印第安人对着干的场景),《合拍》认为戚继光《练兵实纪》的示图(121-125页)与排演舞蹈雷同!
把名将操兵与舞蹈拉上关系是否恰当,对此完全无知的笔者不能置喙,但以清初李渔在《闲情偶寄》所说的舞蹈,则完全对不上嘴。在《歌舞》篇,李渔说:“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习声容也……,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李渔所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日常。事实上,欲“教女子以歌舞”,与沙场演练(遑论战场搏杀)当然相去甚远,不过,看戚将军的操兵布阵图,与排舞(Line-Dancing)拉上关系,确有蛛丝马迹可寻。有点小事可以一提,麦尼尔教授写《合拍》的触机是他于1941年从军接受军训,在他看来,军训演练操兵,与随军乐而动的舞步何异。而纳粹德国、俄罗斯、北韩、中国的操兵以至英国和台湾仪仗队的交接仪式,亦恍如舞蹈。受训在沙场操练发此奇想,让这位未来史学家“分心”研究舞蹈在历史中的角色并写成是书!
李渔所说的“教女子以歌舞”,数百年后的香港亦如此,不由你不信的是,一位经营芭蕾舞学校的退休芭蕾舞巨星告诉笔者,她的同业曾收过不足周岁婴孩的学生(座上众人莫不大惊失色),由菲佣抱着并随音乐“挥动”她的双腿学舞!这名“婴娘”的“舞妈”的目的,也许是希望女孩有朝一日成为芭蕾舞蹈家,但退一万步,当不成舞星亦具“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的优雅仪态!因此是有远见的长线投资。
四
我国的舞蹈,肯定在洪荒时期已深入民间,而且不同民族有不同宣泄情绪的方式,因此舞蹈多元、多姿多采;而舞蹈成为女性“娱宾”的项目,更可追溯至不知何年。《汉书·地理志下》有“女子弹弦跕屣,游媚富贵……”,据《辞源》,“跕屣”是踮起鞋履,游媚则为左旋右转于豪客之间。可知两千多年前女性已懂藉“跳舞”谋生!由于“跕屣”是以脚尖跳舞,此种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舞姿舞步,稍后被学者考出是芭蕾舞源之所本,不足为奇。
不过,由于封建时期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属物,为保私产不失,遂有女子“十二便不出闺门”之“家规”,而达此目的有效手段便是迫女子缠足,虽然《孔雀东南飞》赞美女舞者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然而,以普通常识推断,“三寸金莲”即使出过不少令达官贵人名士诗人墨客伧夫着迷的舞娘,舞蹈仍无法大众化,不难理解(显而易见,如今女性若仍以缠足为尚,秧歌舞、广场舞以至鬼步舞之类的运动舞蹈,肯定流行不起来)。据罗丰原刊学报的论文《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收王子今编纂的《趣味考据》第三册),在舞台上大放异采,令大众神魂颠倒的“胡旋舞”之得名,是“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加上来自番邦,遂被称为“胡旋”。罗丰对“胡旋舞”的出处与在我国隋唐时期始流行的情况,做了极为详尽的考据;更值得注意的是,舞娘亦是“进口货”,她们“和其他中亚珍宝一起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显而易见,这些“进口舞娘”是天足而非缠足。在我国悠长历史上,充满神秘色彩的舞蹈有长足发展;不过,舞蹈之深入民间成为日常文化健康活动的一部分,则肯定在女性缠足已属非法之后!
长话短说(其实是对舞业所知有限无法“长话”),回看香港“舞疫”。跳舞群组所以成为疫情最大受害群体,皆因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舞蹈,除非单人表演,只要两人共舞,便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遑论紧抱对方的贴面舞(漫画《老夫子》所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双人舞,如打“泰拳”,手脚并用,身体接触频频,极为刺激),便难免会受病毒感染,那即是说,“群组”虽然染病者众,却不足以说明带病毒的舞者特别多,因为只要有少数舞者确诊,由于近距离接触,病毒便会广泛扩散。
五
去年疫情蔓延后,传媒对此严重受害群体的深入报道,香港舞业的盛况,方为非舞者如笔者所知。据笔者的了解,当今最流行的舞蹈形式是源自欧洲的华尔兹和南美的探戈舞,都可说是表演为主、娱乐为副、健康次之的舞种。看此间跳舞“学院”的排场,即使场地及配套非常“现代化”,仍无法摆脱上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的士舞者”(Taxi Dancer)经营形式,即是说,进场跳舞者多为单身女性,而驻场候教(待租)的男性舞伴(所谓跳舞“拍乸”——Partner——是也),凭音乐(舞曲)收费,即每曲都有特定价目;由于这种收费方式与“计程车”(“的士”)按定时(里数)跳动的计时表计算车资相同,称职业舞男为“的士舞伴”,既通俗又贴切。应该一提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为帮补家计,不少女性投身舞业,当“出租舞伴”,但她们的称谓不是“的士舞伴”而是“一毫一跳舞娘”(Dime-a-dance girl),以其每首舞(歌)曲伴舞的“公价”为十仙(一毫),因名;而由于这类舞蹈由男伴“揽实”其腰,舞娘有“货腰女郎”的别称,由此而得。
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所记解放前上海多采多姿的夜生活无异,香港在内地开放前,亦有不少类似有“一毫一跳舞娘”长驻候教的舞厅或夜总会,但九十年代内地夜场日多香港的舞业开始式微,至今已几不可见,代而取之的是有“的士舞伴”待“租”的“宴会厅”(跳舞场所),这种转化,凭常识揣断,是男性别有地方觅舞伴而女性因社会条件及种种家庭因素难移玉步,只好在本地觅乐趣;看中此种市场需求,香港遂出现了不少殿以俱乐部、宴会厅、音乐室、健美中心以至演艺中心然而莫不提供“的士舞伴”亦即以招徕女顾客为主的舞厅!
不得不提的是,不少女性于这类场合中觅得“合心水”的“的士舞伴”,便图长期独享,遂不惜出重金把他升级为“私人舞伴”,以月薪甚至年薪“租”下专用;这种情况,颇类把“的士司机”变为“私家车司机”。香港两年前曾爆出有徐娘舞者以亿多元的“终身酬金”包下舞伴的新闻。这宗因钱银轇轕引致的“上流”社会逸(丑)闻,相信并非孤例……
六
因疫情而内情大白于天下的舞厅,十分旺场,生意不因经济瘫痪而萎缩,探其根源,希望今后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撰写论文,为我们作深刻剖析;不过,肉眼所见的表象,亦不难有足以自圆其说的答案。显而易见,香港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城市,“俗人”太多,工商活动金融炒卖频仍的直接后果是“收市”后因“寂寞”而寻求“感情慰藉”,已成这批“有钱人”的常象,而“寂寞”无感情纠结,男女皆有,非常平等。男的为解孤独伶仃的落寞寂寥,既可能赴外寻欢,在香港在内地养女朋友所谓“金屋藏娇”的,相信不在少数;女的虽然大多数做称职的主妇,亦有因为空虚难耐或向乃夫或男友“示威”而各自快活,经济宽裕而擅长舞蹈者,上跳舞学校租个“的士舞伴”欢乐今宵,便成常态。这种另类社交活动,不仅可扛起锻炼身体有益健康的“招牌”,还可换来俗世羡慕眼光而自感飘飘然。

香港舞厅
在公开场合跳舞,众目睽睽,为了自尊、为了取悦观众,舞者莫不悉心打扮,涂脂抹粉加上衣饰或典雅俗艳或纱笼隐约,还有不少年华老去者借“蜡像针”(Botox,此为笔者所译;医家隐晦其名,直译为外行人难解其意的“肉毒杆菌针”)人为地留住青春(动手术去脂漂白除皱纹种眉毛植硅胶更无论矣),围观者大乐,当然亦有人嗤之以鼻,因为她们涣散的“界外效益”(external benefits)不是人人受惠,当然更非人人甘之如饴。无论如何,所有种种,皆令“老舞者”于无意或有意间跌落经济学家所说“炫耀性行为”(conspicuous behaviour)之窠臼。不过,这类女性亦有所得,因为身光颈靓手饰比灯火更刺目,彰显其身家厚重之余,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她们受多金“男方”(丈夫或情夫)的宠爱,这便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代替性炫耀消费”(Vicariou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她们以“实物”表现了家有视她们如珠如宝的“主人”(男女皆有)!
“歌舞群组”确诊者以百计,说明疫情肆虐下舞者仍乐此不疲、迎疫而舞,直至政府出手干预方休;其实,跳舞很易上瘾,如中魔般非大跳特跳不能解忧。约翰·华拉(J. Waller)的《跳到气绝身亡》(A Time to Dance, A Time to Die)一书,记1518年7月发生于法国名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今欧盟议会所在地)的跳舞狂潮,受大流感之苦,数以千计当地居民上街乱舞解愁结,当局劝之不听、禁之无效,如是者大群百姓夜以继日在街上“载歌载舞”凡三个多月之久,结果“跳死”(酷暑缺水缺粮加疲劳)者多达五百余众……跳舞会上瘾,港人有切身体会,香港在疫情下舞情仍未消散;由于潜在需求殷切,疫情过后舞业将趋狂热,不难预期。